《多甫拉托夫》讲述了俄国作家谢尔盖(Dovlatov)在1971年时的四天生活。当时,Dovlatov 已经相当积极地在写小说了, 但却没有在任何苏联杂志上出版。在这四天里, 主人公最终卷入了各种事件当中, 其中每一个都使他得出一个结论, 即作为一个作家, 要走自己的路, 不要听从任何人的劝告。矛盾的交织循环、与布罗斯基的对话、列宁格勒的世俗生活,、西贡咖啡馆、大剧院的全盛时期、lenfilm 工作室…… 这一切使 《多甫拉托夫》不仅是一部传记电影, 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最佳影片(提名)小阿列克谢·日耳曼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杰出艺术成就奖叶连娜·奥科普娜娅
《多甫拉托夫》下载观后评论:
榮獲2018年柏林影展「傑出藝術成就獎」,同時也入圍金熊獎最佳影片的《多甫拉托夫》,是一部以謝爾蓋多甫拉托夫傳紀內容為主的作品。這位以諷刺小說出名,故事發生在1971年左右的列寧格勒(今天的聖彼得堡),那個下著大雪的寒冬,那個在理想與現實生活中苦苦掙扎的文學家真實的生活面貌。故事總會在幾個轉彎處巧妙用上,契訶夫劇本裡經典名言:「一切都會變好」,可悲的是他們都知道未來不會變好,所面對的是無止境的黑暗,以及永不停止的絕望。電影運用大量遠景,大量構畫出屬於那個年代的悲哀,也暗示存在藝術家們內心的悲涼。如同多甫拉多夫最後對前妻說:「我大概永遠都沒有機會出版了,在俄羅斯裡沒有出版品的作家如同從來都沒有存在過一般。不過,不存在就不存在吧,或許我應該改行去當水泥工」這一幕,讓我心痛

6/10。小日耳曼塔建起的政治讽韵和时代珞印布满大大小小的角落,游荡过街景的士兵和载着宣传画的拖车,还有最荒谎的一笔是暗示波兰团结运动的船厂拍摄场地,扮演托尔斯泰、普希金等文学巨匠的群演,参与采访满口积极工作的刻板回答,这个荒无且气候现象永远是云、雾和风的创作土壤,与当局要求撰写美化社会、塑造革命英雄的报道形成鲜明讽刺,多甫拉托失的生活比普通人的日常更加被无趣和黑色幽默所包围,例如把一个爱情幻灭写不出诗的石油工人拉到化妆舞会,或者送酒讨好一个误认为是作协大人物的尿道医生,时不时假装秘密警察让不醒酒的小贩纪录买禁书的人员名单,他常驻足出门框外,象征无法融入的距离感,从中汲取惰懒的虚无主义思考,漫步于一个不为钱和名誉只为传递真相的文人黄金时代。

在斯大林时期,布尔加科夫无法发表作品,最后他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说,“要么给我一份工作,要么把我枪毙”,最后斯大林没枪毙他而是给了他一份莫斯科某剧院的杂役工作。如今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世界公认的杰作。捷克的赫拉巴尔某段时间内也无法发表作品,身为法学博士,却干着底层的工作(打包工,钢铁厂工人,剧院杂役等等),他说他为了写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决定作家能否发表作品的不是某个人,不是作协(在那时的俄罗斯,作协实在是个荒诞的存在,现在在中国也是),而是作家自己的文字以及读者认同。还有一种情况:不论发表与否,作家一直在写作(艾米丽·迪金森,佩索阿)。可如果不能发表没有读者,作家的写作是否还有意义?要去读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小说。

前些日子读完了多甫拉托夫已绍介进中国的两部作品,现在偶然看完这部就有些不一样的感触了。或许是有些主观打分,三四星皆可,还是评四星好了。不过男主的演员人选实在值得吐槽…哎。和我心中的形象很不一致,略有出戏。场面调度始终克制而收敛情绪,像是旁观者在静静凝视另一群旁观者。所幸对苏俄文学史和我国类似政治环境下的伤痕文学略有了解,即便调度显得冷静还是挺有感触的。部分长镜头有些拖沓,整体ok。低对比度的浅焦画面自始至终都营造着梦境般的感觉。没有抗争、没有愤懑、没有悲伤的歇斯底里,只剩下长叹,似乎已经被麻木化了……可是终究、语言永存啊。哎。对所有高压环境下不得志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我实在是无法客观评价。

非常差。拍的不是多甫拉托夫,而是导演yy下的一个极权体制下的异见作家的四天。而且关于苏联基本的一些服化道都搞错。imdb第一条影评说的很好,多甫拉托夫不是索尔仁尼琴,他没有跟体制作斗争,他安安稳稳地活在体制里面,通过合法的手段移民美国。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比索尔仁尼琴一更有力量,更humane。我觉得这才是多弗拉托夫的魅力所在。不抗争且说实话的气质。这种气质非常sutle,没有生活中极权体制下的人很难理解,但即使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也不是全都能理解。不带有任何预设立场地真实的描述人的生活与极权的关系,需要天赋和勇气。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这份天赋和勇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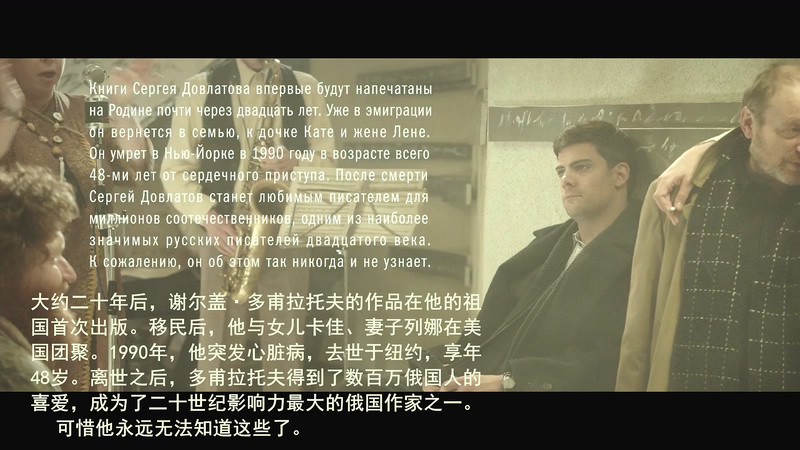
3.5,比起为革命斗士立传,更像是对存在主义的反证,因此叙事没有侧重于谢尔盖,抑或他身边那群失意的文学青年,而是近乎虚焦的背景:列宁像,铁皮船,浓雾氤氲的街道,以繁多符号勾连起一个极权倾轧、理想主义式微的昨日世界,从构图,转场到幽灵般的长镜头,调度技巧释放于无形,恰如这片土地上举世闻名,却被迫噤声或流亡的面孔,时间的飞逝了无意义,只是平添在铁幕下行进的乏力感。相较于在政治背景上飘忽几笔的《盛夏》,其间的萧瑟沉郁、对宿命感的传达更甚。不过,部分台词和心理描写还是偏弱,文本中静置的诗意过于散碎,没能朝前流动起来,人物间的镜像设置也略显单调。
非常震撼。地下沙龙的人从不谈论生活,因为生活毫无意义;遵循环境和制度的人们,也懒得谈论生活,因为生活毫无意义。真实对应的是苦难,虚伪却能拥有幸福。这样的处境,想真实地活着的人该怎么进行?这里面最让我赞叹的,是影片并没有将这两类人群脸谱化,每个人之间的界限似乎清晰可见,却又模糊不清。虚伪活着的人,却又欣赏甚至愿意以某种方式帮助真实活着的人。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它们最终要等待骤变。因为他们拥有最强大的力量,那是在如此绝望的环境下,还相信自己仍然存在着,于是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真诚地活着,真诚地做着错事,执拗地不过任何虚伪的美好生活。
早就听说过前苏联导演阿列克塞日耳曼(1936-2013)的名字,他一生只拍过五部电影,三部被禁演。前几年在影展里看过他的《二十天无战事》,不同凡响。今天终于看到他儿子小阿列克塞日耳曼(1976出生)的这部新片。它描写两位七十年代离苏赴美的作家(一位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的作品90年代后在俄国大红)几天的生活状态,角度独特,影像生动。表现上世纪70年代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后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归年代”,将那时文化界的压抑、禁言、迫害;苦闷、骚动、颓废等气氛描写得十分到位。时隔近半个世纪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对得起他们的父辈和时代。
如果从宏观角度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归类为俄国文学的话,加上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也算读过几本。无论是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学就像其国土一样“著作等身”。文学巨擘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触及的彼岸是因为其历史凝炼的恢宏,那诸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生存与命运》则更是加持了历史悲剧的共鸣。他们有没有“伤痕文学”一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伤痕和他们太多像似,而且,我们的伤痕在经历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大有“旧伤未愈又要添新伤”的态势。 @2018-11-25 13:13:42
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懂一点俄语,好能从语言的细节里分辨出哪些是宣言式的权力话语,哪些是刺人也刺己的苦涩讽刺,哪些是真实的情感释放。不过我猜小日耳曼的风格确是在取消这些细微的区别。带着柔光效果的长镜头滑过一个又一个场景,好像是在发梦,又像是在带着感伤而缅怀。这和多甫拉托夫真实生活里的艰难大相径庭。不得志的艺术家哪里都有,可影片如此寡淡如此间离的处理方式让他的挣扎既不像西西弗斯般富有存在主义色彩,也没有抗争式的愤怒,只剩下一些磨平了的苦涩感,放在嘴里如同嚼蜡。说不定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时代精神:一种麻痹了的宿醉感。
很久没有看过这么棒的电影了。迷雾之中,布罗茨基和多甫拉托夫在一阵寒暄之后背道而行,前者迫于压力去了美国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者留在了苏联,作品也只有在死之后才被人们慢慢看到在一个人人自危,压抑自由与人性的时代,当局者在自封为神,普罗大众在渴望英雄,创造千篇一律的英雄故事,或者试图幻想回到以往的辉煌时代的方式逃避世界,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去默无声息地思考,无论何种境地都诚恳地活着,不迎合也不谄媚,虽这片土地让它处处失望,但他还是照样坐在那里,听爱着的人们唱歌,读诗,发牢骚,在烟雾缭绕之中默默微笑。
如果从宏观角度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归类为俄国文学的话,加上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也算读过几本。无论是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学就像其国土一样“著作等身”。文学巨擘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触及的彼岸是因为其历史凝炼的恢宏,那诸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生存与命运》则更是加持了历史悲剧的共鸣。他们有没有“伤痕文学”一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伤痕和他们太多像似,而且,我们的伤痕在经历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大有“旧伤未愈又要添新伤”的态势。
也许是他最难的时候吧,与妻子离婚,作品没人欣赏,也没人愿意出版,整天被迫接一些记者的活,写一些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贫困潦倒,为了给女儿买洋娃娃而去做走私生意赚钱。虽然经常出入文艺圈的聚会,可是相互欣赏能聊得来的人极少,处于人群中却十分孤独,看见不得志的作家自杀,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感觉人生没有出路,甚至考虑放弃写作。后来他移民美国,作品得到非常多的人的认可和喜欢,可惜他才48岁就去世了,直到死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人喜欢。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潦倒作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