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n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成为作家是他的梦想。在回到故乡安纳托利亚之后,他使出全力筹集资金以出版自己的书籍,但却忘了父亲之前也负了一笔巨债……
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金棕榈奖(提名)努里·比格·锡兰
《野梨树》下载观后评论:
和《冬眠》比稍微刻意了些,“野梨树”统领了电影的多个象征,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个他眼中的农民呆的地方,他恨这里的一切,这里的朋友、风景、家人,最好原子弹炸掉或者躲进木马消失掉,短暂的秋季,他做的不外乎是出版自己的书,要努力找到自我存在的证明,又要与这个家乡划清界限,父与子是锡兰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但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交谈却少得可怜,到最后结尾的那场交谈,儿子似乎明白了父亲的挣扎与自己的抗争的同质性,他们都是一样的人,父亲的选择逃避麻木,与自己的愤世嫉俗在这个冬天汇集在一起,父亲成为了他实际上的唯一的一个读者,父亲终于放弃了那口不出水的井,儿子却成为了曾经的父亲,这口井一定能出水,锡兰的理想主义的幻灭是土耳其国家压抑的表征,年轻人不得不面对遥不可及的偏远的东方,在那里走出人生的新生

锡兰镜头的高级之美,是那类你盼着他能多拍几处空镜头的导演类型,但他却在偏偏站在景色之外,以相对过载的文本量与他的角色紧密地贴合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本片的自传性色彩过强,整部影片都与这位文艺青年生产着一种不多见的默契,默契得连他那自命不凡、愤世嫉俗的不着调的瞬息都被拍得极具认同感。乡野之地的野梨树们“不适、孤独、扭曲”,像极了曾出发城市又选择回归乡土的小镇青年们,他们的处境如同锡兰一般不尴不尬、不上不下,不被家人理解的同时又受缚于家人。在这个意义上,井绳、蚂蚁、甚至于树下一次偶然的亲吻,成为了平庸之苦的缓冲物,助益了锡兰们乡愁与理想的精神跃升。这种行云流水的日常感来自于他们失却了清晰的反抗对象,因此力量感并无力感都尽数消解了,这平淡的困境本身是无解的,故事以外的其他人又何必假意编纂解决之道。

散漫的叙事,一如既往的冷静和疏离,哲理思辨贯穿其中,犹如理想主义的挽歌,影射土耳其青年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既是“奥德赛”时期,同时也可称作“过渡间隙感”——“父辈权威与子代意志的矛盾导致子代在反抗与被规训之间往复挣扎,这对稚嫩的个体是严峻的考验,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井作为核心意象代表传统功能—未来生机,贫瘠的状态一如Sinan的遭遇的现实。特洛伊木马梦境指向急切需要被承认的渴望、两段梦境的死亡意向:蚂蚁婴儿/自杀。掘井的仪式感,父子同是畸形的野梨树,荒谬地下掘迎接苦难的未完成。视点的几个转换(无人机?)很奇妙,尤其是树下的段落,从窥视女人到凝视男人,直面他的尴尬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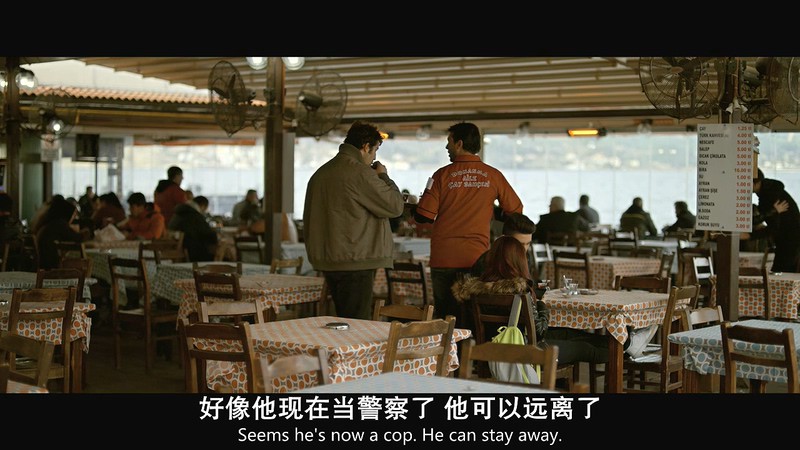
一个文学青年的自画像——愤世嫉俗,目空一切,无所事事,终日晃荡,前途迷茫,彷徨苦闷——刻画得太准确了。他误解父亲:生活的失败者,拖累家庭;他用卖掉父亲最爱的狗的钱出了自己的书,和母亲一起嘲讽父亲因丢失狗深夜黑暗中独自哭泣,很多错不会被坦白;他在给母亲的书上写着:献给最亲爱的母亲,一切都归功于你,就你一人;父亲被认为是缺席的、不负责任的,最终他的书只有父亲一个读者,放在书店里一本也没卖出去,他还发现父亲的钱包里还夹着报道他的书出版的剪报。结尾看起来是两种结局:一是他终究受不了内心的愧疚,在井中自缢;另一种是在纷纷的大雪中他接续父亲挖那口井,那个仰拍的镜头意味深长。

给锡兰的第二次机会,爱上了。自恃清高的知识青年回归农民家庭,为自己前途争取的同时还要面对赌徒父亲和贫困日常,他贬低这贫困家庭却以儿时的野梨树作为心灵寄托,“赞美当地生活文化”,一个热爱文化却又渴望别处的青年人物被188分钟撑得丰满、残忍又真实。土耳其的乡村那样令人熟悉,泥泞的小路、喧闹的野狗,遇到一二同龄人就畅谈起空中楼阁,与爷爷长辈聊天便心不在焉讥笑他人。强烈,强烈共鸣的同时,感恩导演用影像构想的几种可能,回归的小猎狗、吊死的父亲、井中自缢的自己,而在这几种可能外,导演仿佛给予了对我和青年的救赎,给了他理解父亲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理解那野梨树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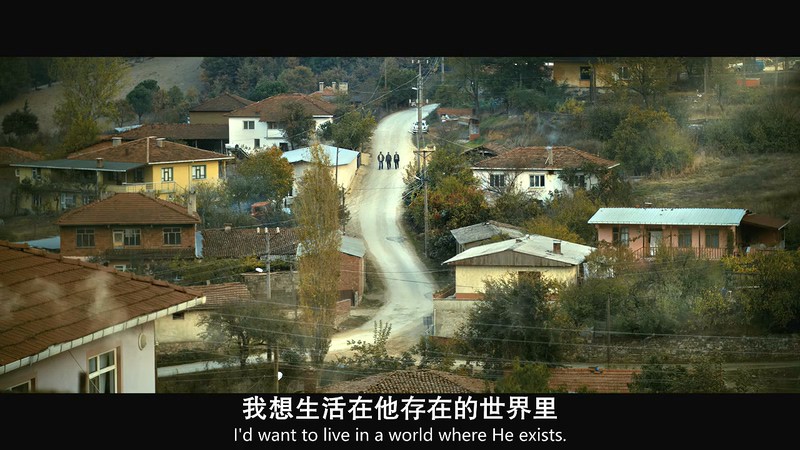
三个多小时的时长,大段的人们对话,看似与主线神离的家庭琐事,导致观赏的焦点放在了极致的摄影上。这自然是锡兰想到的,在视线聚焦这个无名的村庄,在各种观点的交织中拾取碎片来思考。家庭关系、父子感情这条主线一直延续着,像极了卡夫卡。卡夫卡至少出现过三次,书店的照片、父亲说的“没有审讯的判决”,以及最后幻香中儿子在井中自尽。围绕每段对话都可以谈论很多,这正和儿子心路历程是一样,一番探索后,才能无言地体会到世界上仅有父亲是能理解他的人。这就是反面的卡夫卡,父子关系总有阳光的一面,即使在大雪中也能感受到的温暖。片子最妙的一个镜头下展现的时间位移,这比剪辑巧多了。
前大半部的叨叨追問,出自一個吊兒郎當,肩不能負,無法承當,面孔游移的近乎小人,讓我很覺莫名,因為其實問題都很好,但發問的人不好,在我看來便全盤皆輸,以至不知所云。看到作家大力回懟一段,竟覺暢快,這就讓我疑問,導演為什麼想拍這部電影,為什麼要以劇中主角的角色反复設問?主角這樣的面目,不耐看,也不經看,提出的問題,也都憑空而起且無疾而終,只有背後的群相,還耐揣摩。最後浪子回頭一段,嫌俗,問題還是,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敘事?叨叨完三個小時,似沒有能剩下的東西,予人深沉一擊的東西,無論是智性的,還是感覺的。
无奈地回到一直嫌弃的故乡,苦闷的小镇青年想重新认识她却发现一切都变掉了,想描写在地的生活方式而当地人的观念早已被国族主义和全球化裹挟。失掉尊严的父亲、走失的狗、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阳光,黄色和棕色令人绝望地蔓延。前面节奏太慢看得有点昏昏欲睡,直到文学争论以及家庭冲突台词逐渐加密,才让人兴奋起来。而野梨树下开始的那场关于宗教的功能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辩论带来一段长时间的观影高潮,也为最终父子关系的和解埋下伏笔。锡兰如同西西弗斯一样敲打着石头,最终认可了自己血脉中固执的传统,给日常的荒谬赋予了意义。
下雪的时候看锡兰是纯粹的享受。摄影和台词满分。看的时候在想我和我爸,故乡,虚无缥缈的文学幻想,刚刚结束的一段令人不适的人际关系。儿子和父亲渐行渐远,但却越来越相似。我们想远离这个正在腐烂的故乡,我们写东西,我们做梦,我们都是不适应环境的孤独的畸形的野梨树。最喜欢躺在野梨树下的父亲浑身爬满了蚂蚁又突然睁眼以及俯视结尾挖井的儿子的镜头。那一瞬间突然好感动。那个满腔怨愤怼天怼地的儿子已经死了,把自己的过去吊在井绳上,然后挖井,“向地球中心探寻”,寻找自己的未来。文艺青年永远活着,他们在山上挖井。
8.5,坠入锡兰视听的温柔乡,沉稳且优雅。正如开场脱离缰绳率先进入地球中心的石块,小镇待业青年到达挣开旧环境的岔路口,抱有热情甚至自负的憧憬,展开与各阶层各年龄段密集且附有哲思的谈论。信仰,宗教,人生抉择,社会秩序,锡兰用较为日常的形式冲淡了说教意味,加入不常见的梦境描写,同时也以<野梨树>书名的互文代入和审思自我。父子关系作为隐线穿插在这种形式的探寻下,几番对话写实但暧昧,直到出书才骤然跃上文本,以单线隐喻全篇野梨树的独特意义,共情与雪花同时落地,我们都是孤独,畸形,但且有价值的人。
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艺青年,看不起周围的一切,对身边的一切都有几分厌恶,想突破想逃离;可最后理解和关心他的只有连他都看不起的父亲。这和你我的故事何其相似。对于精英主义反思和讽刺,可问题是反思精英主义这件事本来就很精英。不喜欢的最主要原因是,台词对白真的太多了。和初恋女友,和成名作家,和老朋友,还有和新的教工。我能看出这是主角在一次次寻找慰籍和突破,但真的毫无设计和享受感,到了最后的三人谈话我已经看不进去了。PS.之后可能会再看一遍,我看的这版翻译真的太差了……
当一部三小时的“絮语”电影找不出一句“金句”的时候,对话也就成了“无意识”的填充物。以《小亚细亚往事》为界,锡兰不再纠结世俗伦理,转而雕琢一种困顿之境。大量引入文学/宗教话题,然而并非辩证,只是施以同情。不具扩张性的电影语调又与画面互为镜像,是缘井求源、是兀野一树、是虚化背景前明暗斑驳的脸。从来认为他的电影没有人物,是拟态化的自我观察,他在寻找一条边界,自传与虚拟、脱困与自囚、此处与彼处、反叛与继承。某种程度上他已与帕慕克合体,都是金角湾斜阳中的游吟人。
非常有文学感的一部的电影,但是作为一部文艺电影来讲我觉得电影在探讨一些内容的时候,单纯的就是从一些人物对话进行,但对话又不够精炼,反而非常的冗长,单纯就讨论而讨论,而他讨论的主题在之前拍摄的部分其实又铺垫不够,所以一旦到长对话开始进行一些哲学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学术主题探讨一样,不能get就会觉得很枯燥无聊,失去观影兴趣。但是影片中的一些暗喻和风景还是拍得很漂亮的,这可以夸奖。所以基本上还算能看吧,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尤其对哲学不感兴趣的人。